
(班班多杰老师接受采访)
我的家乡在青海宗喀地区,就是现在的西宁市湟中县塔尔寺地方。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,我就上了青海民族学院附中。青海民院以前是大学,1964年因为要培养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积极分子,就把大学撤了,办了一个翻译班和一个师资班,专门为牧区培养翻译人才和中小学老师。我是师资班班长,初中毕业后学了两年,1971年中专毕业,正赶上中央民族学院在全国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。当时的青海民族学院正想恢复大学,十分缺少教员,想自己培养一批教员,就从我们这批毕业生里选了几个所谓成绩好一点的学生,直接送到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来学习。我1971年11月来,1974年9月毕业时学校没让走,我就这样留在了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教研室当教员。当时吕大吉教授、佟德富教授都是我们一个教研室的。
我是藏族,从小学习藏语藏文,因为那时实行双语教学。开始留校时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大家都向科学进军,都想搞自己的专业。当时我也不甘落后,也准备在教学和科研上有所作为。这时候,佟德富、余敦康以及哲学教研室的老师们就提醒我:“班班,你应该研究藏传佛教哲学。你的专业是藏传佛教,你的哲学基础非常好,既懂汉文又懂藏文,你以后要是搞藏传佛教哲学的话,那要比别人强得多。你要搞别的哲学,估计你赶不上人家;但搞藏传佛教哲学,对你来讲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。”他们这么一提醒,我觉得太有道理了。于是我一边教哲学课,一边去民语系藏文教研室跟着当时的研究生班听古藏文课,为研究藏传佛教打基础。
当时学校从西藏调来了一个活佛,叫东嘠·洛桑赤列教授,在民语系藏文教研室主讲藏传佛教史、藏族历史、藏族文化史。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一个非常著名的活佛,1947年在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学经,毕业以后参加了“拉然巴格西”答辩,取得了“拉然巴格西”的学位,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学位,因此学问是很大的。六十年代初,学校根据周总理的指示,于1961、1962年办了两届古藏文研究班,因为需要高水平师资,就从西藏请来了好几位专家和学者,东噶活佛就是其中一位。他善于接受新生事物、善于学习、思想非常敏锐,到了北京以后,他又学习了汉语文,同时,还研究了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有关思想,实际上就是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,他还提出了现代教学方法。因为在大学里面教学和在寺庙里面教学毕竟不一样啊。所以,到北京以后,他学问增进很快。一方面呢他在传统方面基础非常非常好,传统的藏文化非常深厚,另一方面呢,他又吸收了一些现代的理论,现代的教学方法,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体现得最明显。可惜,“文化大革命”发生以后,东噶活佛在北京就待不下去了,后来就被遣送回西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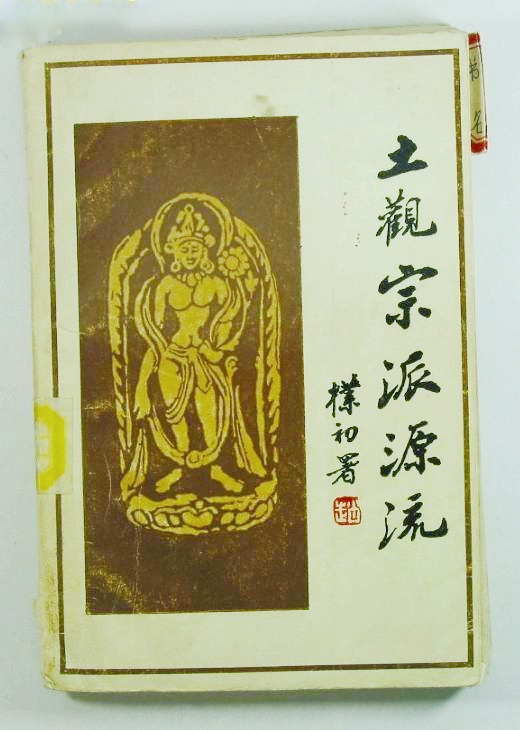
改革开放一开始,我们学校又把东噶请回来了。他1977年来的,1978年开始上课。那个时候我们招了研究生,招了古藏语研究班,他一来就投入到教学里面,给研究生、古藏语进修班学院以及老师们上课。他上起课来传统和现代结合,每次上课,我都得到很多收益。我跟着研究生班随堂听课,他的藏传佛教史课我一共听了三遍。这门课用的教材是《土观宗派源流》,这是清代一个土观大师写的,写得非常好。原文是藏文,后来刘立千教授把它翻译成了汉文并加了注释。刘立千是大家,三十年代就从四川进入了甘孜藏族地区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,后来在当地娶了一个藏族媳妇。这部书是他四十年代在康定学习藏传佛教的时候翻译的,译得非常好。我每次听课都做很详细的记录,最后把这个记录整理出来,认真消化、认真吸收,还结合这个教材认真学习。在东嘎先生授课和教材的基础上,我又搜集了很多和藏传佛教思想史相关的重要的藏文资料,花了近十年的功夫才写出了《藏传佛教思想史纲》,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。这书算我的第一本著作,早期的一个代表作。任继愈先生给写了序,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,这是我研究藏传佛教的一个基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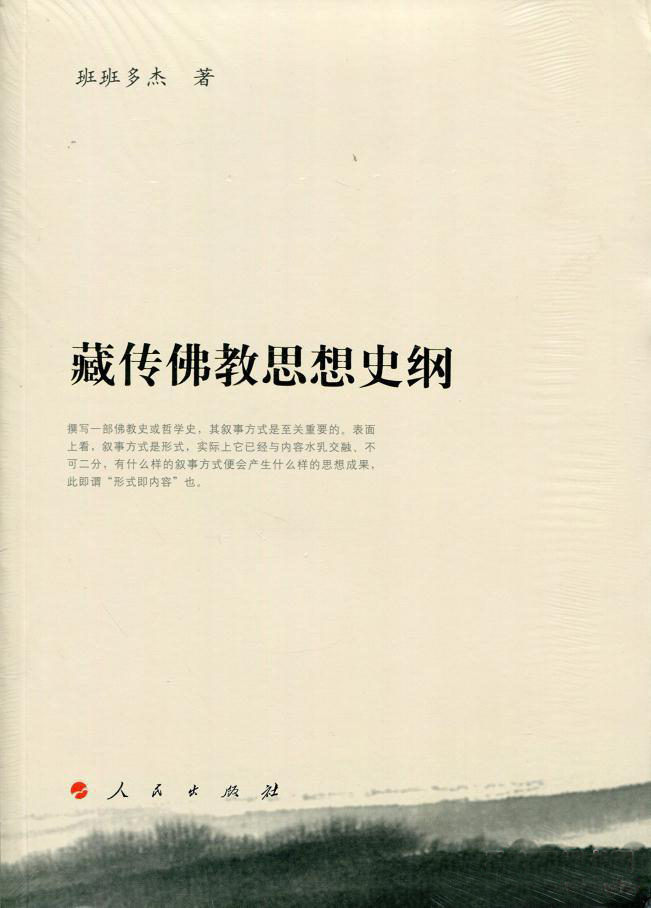
1978年年初,当时西北民院的文从志老师把我引荐给白塔寺的法尊法师,这样我又跟佛协的法尊法师学习。法尊法师是汉族人,1902年生人,老家是河北深县,他最早可能是在上世纪初在五台山出家,后来到雍和宫学习藏文。1924年到四川甘孜的贡噶山去学习藏传佛教和藏文,后来又到西藏求学。他在藏传佛教、藏传佛教史以及将藏传佛教的经典翻译成汉文方面,在国内可以说是第一人,是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翻译的大家。
法尊法师圆寂之后,我又跟观空法师、郭元兴居士学习。观空法师也是汉族人,1905年出生,和法尊法师是同学,一起进藏,一起去学习藏传佛教,他们在五六十年代都是中国佛学院的教师。郭元兴居士藏文也非常好,是赵朴老的秘书。跟法尊法师、观空法师、郭元兴居士学习,使我对藏传佛教史的认识有了很大提升。1981年前后,我又通过我们系樊先胜老师的热情引荐,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立天先生,于是又跟方先生学习怎么用现代的方法去研究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,得到很大的帮助和支持。我写的第一本书,他认真批阅修改,并在《中国日报》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书评加以推介。没有这些大师的帮助,没有他们的宝贵指导,肯定没有我的今天。
在我求学治学过程中,还有需要提及的一点,就是牟锺鉴先生等前辈对我的影响。他调到我们系以后,我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。还有吕大吉教授,七十年代初我入校当学员的时候,吕老师给我上过课。后来他调到宗教所,然后又调回来,但一直住在咱们家属院里。从1998年开始,吕老师、牟老师、还有我们好几位组成了一个爬山队,一周组织一次爬香山,时不时地还加入一些大学者,如于东康、戴康生、葛荣吉等先生。爬山既是锻炼身体,又是学习的难得机会。因为吕大吉、牟钟鉴等先生不光爬山,一路上他们几乎不停地在热烈地、无拘无束地谈学问、讨论学术问题,我们跟在身边当听众,偶尔也插话,请教问题。这个机会在课堂里是得不到的呀,他们在课堂里边不可能把他们的真实想法、学习的方法全部都给你倒出来。爬山的时候很随意,时间也很长,一般是中午一点从家里出发,一直到晚上七点才到家。我们整整坚持了12年。这十几年的爬山对我来说受益太大了。
我在写了第二本书《拈花微笑——藏传佛教哲学境界》之后,就比较系统全面地投入到了藏传佛教的教学和研究中,并开始进入了藏传佛教专题研究,因为通过写这两本书,对藏传佛教各个哲学宗派的思想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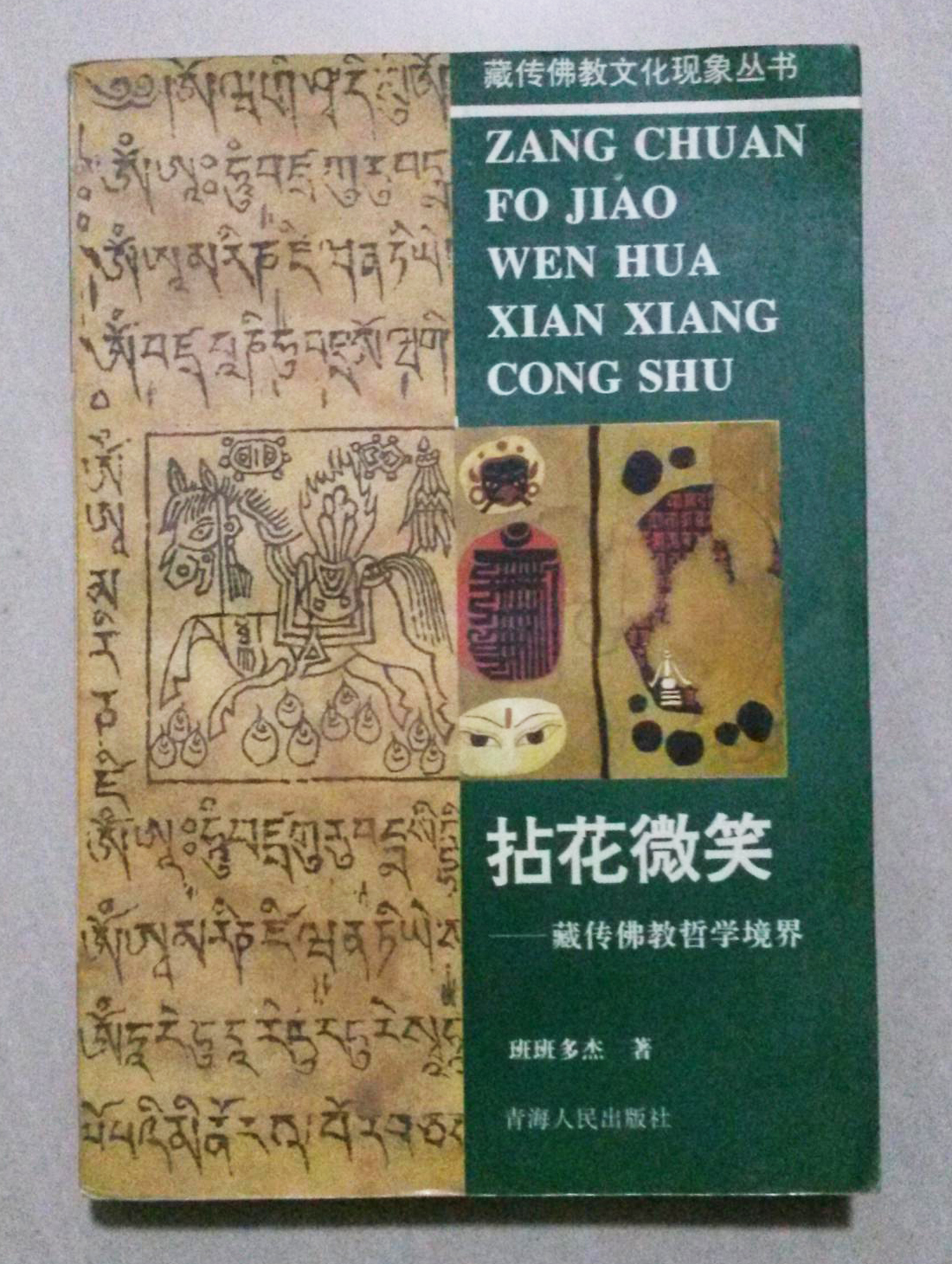
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,怎么样进行专题研究,使这个研究向纵深发展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在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,我采取各个击破的打法,专题研究藏传佛教史上的每一个宗派。首先研究的是萨迦派。为此,我到过西藏,到过萨迦寺,专门请教过萨迦寺的一些高僧大德,也接触了论述萨迦派有关哲学思想的有关藏文经典,写出的一些专题文章,我还请方立天教授指导过。方教授看了以后,提出了很多意见,经过修改,最后在《哲学研究》上发表了。接着,我研究宁玛派,关于宁玛派大圆满法的专题思想的研究成果,也在《哲学研究》发表了。后来又转向了觉囊派的研究,其中对这一派的经典《山法了义海论》的研究成果,在《中国藏学》连载,已发表12篇,最后一篇正在写;还有一篇在《哲学研究》上发表,觉囊派的研究算告一段落。
目前,我正在研究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思想。关于格鲁派的思想,我在《哲学研究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在别的杂志上,也发表了多篇。其中关于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思想,我写了一本《宗喀巴佛教思想评传》,估计有40万字,准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,我也已经交稿了。现在关于噶举派的思想还正在撰写,随后将陆续公之于世。
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,前年我成功申报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,叫做《藏传佛教思想史资料选编与藏传佛教思想史论》,现在正组织研究。我们有一支十几个人的团队,主体是我们学校哲学宗教学学院和藏学研究院的,还有北大、青海民大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专家。关于资料选编,有三个方面的资料:第一是我自己翻译积累的。我研究藏传佛教将近40年了,期间翻译了很多资料,一部分我在写文章的时候用到了,但很多资料还在“睡觉”呢。我准备把它整个整理出来。另外,近代以来,像法尊法师、观空法师等高僧大德也把很多藏传佛教的藏文资料翻译成了汉文,这是第二个资料。第三个资料,是组织再翻译一批,我们自己在翻,也请了一些朋友在翻。目标是搞出一个三四百万字的藏传佛教资料,按照藏传佛教年代顺序和发展脉络,把它编出来。这是课题的第一项任务。第二个呢,就是以这个资料为基础,写出一个藏传佛教思想史论,前史后论。这样就完整、就珠联璧合了。一个是资料,一个是史论,我们力争把它做成我们学校科研成果的一个品牌吧。
(本文根据2016年11月10日张龙翔老师对班班多杰教授的访谈资料整理)
